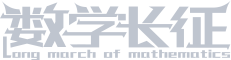弦
弦
月明中
本文作者Adaurora(月明中),数学长征已授权发表,发表时稍有改动.
「你这叛徒!自然一定是和谐而美好的!」
这位在外流浪多年的门徒何能想到,自己竟然会在回希腊的船上被曾经的友人发现。
「万物皆数……几何沉思使人解脱,而音乐净化灵魂……」
在海水的浸没中,万千思绪挣脱了缰绳,在希伯斯的头脑中冲击、回旋、碰撞着,交织成了一团。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老师,看到了那位充满智慧的贤者,那位时常优雅地弹奏着里拉琴的贤者——不过在下一秒,那份优雅消失殆尽——他看到了恩师脸上难容的怒火,听到了暴怒的斥责与诅咒。
风亲切地抚摸着此时绸缎一般柔和的海面,而太阳热烈地温暖着它。垂死的哲人身躯下沉,在暗中涌动的滚烫沙砾间终于停止了呼吸。
「频率和琴弦的张力也应该不成正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希伯斯这样想——不过他已沉没在地中海底,没人会知道了。
毕竟弦就是弦,只有人才能将其奏响。
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也太过诡异,一段华彩乐段过后,包括演奏者在内的全场听众都无端端地昏死过去了。不过那些溺死在水中的人和事,终究会渐渐被世人遗忘吧。
故事就从那天晚上讲起。
青年学者塞西利奥像往常一样,在结霜的夜拉起他的小提琴。这是一把名贵的克雷莫纳制小提琴,已是略略陈旧了,琴身稍显斑驳而渗着丝丝缕缕松香的气息。
夜风在琴弦上徐徐流动,音符在琴弓上奔跑跳跃,他演奏的是帕格尼尼的b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那琴声宛转悠扬,似水而更似烈火,琴弦的振动动人心弦。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塞西利奥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一位水平卓越的小提琴演奏家。
这炫技性的曲目本应十分耗费体力,但他却享受而放松——他太需要切换自己的思维方式了。近来,他把全身心投入到了研究中,解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偏微分方程。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用粉笔在黑板上进行演算。那一行行密密麻麻的白字恍若经文,同样使人头晕目眩。他也随性,黑板随用随擦,不到必要时懒得进行清理。他是那样投入地研究,终日在尘雾中钻研,以至于不知不觉间身上又蒙上了一层粉笔末。
幸而在一个小时前,他完成了论文。付出的心血终究浇灌出了果实。他的这个研究倒是和他对弦乐器的狂热关系密切,他发现:弦振动的频率竟然可以是虚数——负数的方根!
最初,这个结论是在他求解另一个问题时无意发现的。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他以为这只是窗外的喧哗声使他无法专心投入而产生的错误。虽然这个结果是如此的出人意料,但是他在后来的反复验算中,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那一天,他不理睬窗外愈演愈烈的喧哗声,将那复杂的验算过程进行了无数次。他甚至用掉了好几盒粉笔,也都找不到自己的计算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而在研究中,他再次有了惊喜的发现:虚数频率其实同样有物理意义。我们知道,复平面是实数轴的高维扩展,而虚数频率则可以用来表示弦在高维空间的振动!塞西利奥推算出来,在四维的闵可夫斯基空间中,这将会表达为梦幻般的超距作用!而这种虚频率的振动,如果只是想不加控制地实现,也非常简单。
一个使人产生无限遐想的理论就这样萌芽了。塞西利奥感到无比振奋,这也正是为何刚刚结束研究没多久,他就演奏起如此欢悦的协奏曲。超距作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理论还尚未成熟,但他相信自己的发现能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将会改变时代!
一曲终了,窗外又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差点忘了解释:之前,现任总统泽维尔先生多次表达了「建设和谐而美好的美丽新世界」的志愿,开始了各地的视察工作。明天,他就将到本地来参观视察。这是人们从半个月之前就一直在组织排练的,以欢迎他的集会。
说到泽维尔先生,每天的新闻都是会提及他的:诸如「泽维尔先生支持修改税收法案以加强公共建设」「泽维尔先生支持延长工作时间以促进经济发展」……
这些标题看似冠冕堂皇,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在这个社会上,多数人劳苦终日,而少数人坐享其成。而那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宣扬着他们所谓的爱国,让多数人中的多数人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但实际上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时有发生。多数人在繁忙高压下终日劳作,汗水在田地和生产线上流淌,而他们却拿着高额税收下低薄的薪水。以此支撑的政府收入,相当多的一部分被用于所谓的外交,而更有一部分去向语焉不详。然而他们中的多数却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看到了泽维尔先生在电视荧幕上出现,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泽维尔先生的领导绝对正确。看看这些可怜人吧!宛若工蚁被信息素支配着一般劳苦终生。
至于反对者呢?泽维尔先生早就安排各种罪名,暴力消除了大部分反对者。泽维尔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巡视,也许正是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同时他身边也有着严密的安保措施,成群经过严格封闭训练的武警保护着他。他也知道,平民中尚会有一些他的反对者存在。
塞西利奥便早对泽维尔先生心怀敌意了。他本也出身名门——那把名贵的小提琴便足以证明。然而早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过高的民众支持率引起了泽维尔先生的不满,以贪污的罪名被控诉而被终身监禁了。一年后,他父亲被宣告在狱中自杀身亡。
无论情况是否属实,幼小的塞西利奥心中留下了仇恨与阴影。他永远都忘不掉那个雨夜——父亲在冷雨中被强行押走,而自己只能抱着琴无助地痛哭——他永远都忘不掉那个雨夜。那时他第一次发觉,自己就像一根即将崩断的琴弦。
就如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样,父亲入狱后的小塞西利奥被软禁,并且再没见过家里人。他的生活和教育都由政府负责。不过,他展现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艺术天赋,得到了赏识者的培养和保护。时至今日,他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青年教授,也是知名的音乐家——显然他这样的身份是无害的,也没有表现出攻击性,泽维尔先生并没有在意。
然而,完全不在意也是假的。说来戏谑,明天塞西利奥将作为演奏家,被邀请参与总统欢迎晚会的演出,他无法拒绝这个也许带有讽刺意味的邀请——当然,大概也没有人会拒绝他这人间难得几回闻的精彩独奏。总之,他要去,并且不得不去。泽维尔先生当然也不会怕塞西利奥会对他有什么威胁——不知多少全副武装的刺客被他的安保系统暗中处理掉了。
此时的塞西利奥听到了窗外再度传来的喧闹声,便想到了泽维尔先生招牌式的假笑,想到了明天的自己,也想到了永别的父亲。他一时悲从中来,难过到眼眶泛红却流不出眼泪。
他想为父亲复仇,可他什么都没有。明天,他将通过几乎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安检,能陪伴着这个瘦弱青年的只有一腔孤勇和他的一把小提琴。
一把小提琴!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抱着决志拿起琴和弓子,以和平常不太一样的方式,先是连续拉了三个轻快的跳音,又回拉一顿音……
霎时间,从打开的粉笔盒里,从他身上,也从他身后尚未擦去的演算过程上扬起了粉笔末的尘雾,在不太大的房间里飘散弥漫。他终于能流出眼泪了——同时他也笑了。
第二天清晨,塞西利奥拿上他的琴,轻轻掩上门出去了。一缕细微而清澈的晨光透过雾霭投在了礼堂中众人正等待着的他身上。
塞西利奥他自己也没想到,数学和音乐以这种方式完美融合,且这么快就能改变时代。
后来法医的鉴定结果是:泽维尔先生死于脑干出血。